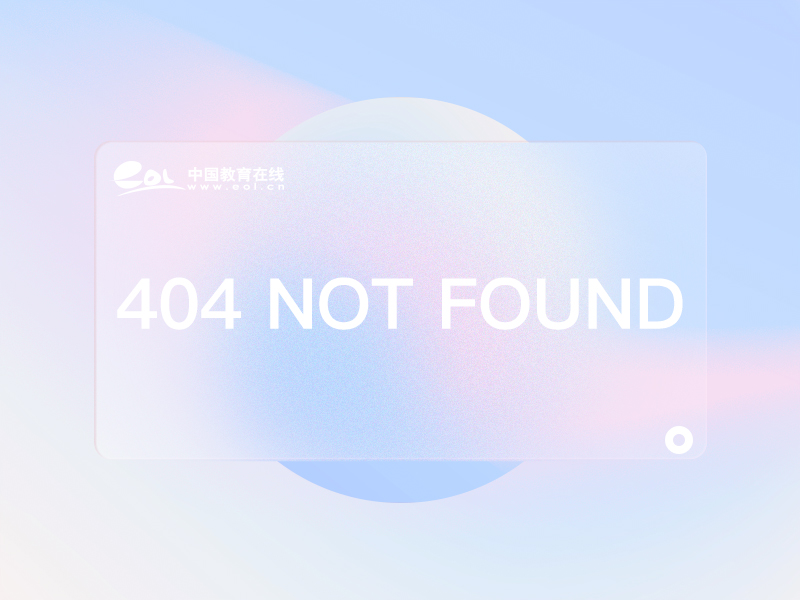
《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坦承了哈佛存在的不足
我们对刘易斯深怀敬意——正如哈佛教育学院霍华德·加德纳所说,刘易斯是一个勇敢的人,写了一部大胆的书。这是作者作为教育家所具有的责任感的驱使,也是美国良性的教育生态和宽松自由的言论环境的客观写照。
哈佛:勇敢地反思卓越
《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一书的书名,就告诉我们这必是一本理性而大胆的书。哈佛大学是当今世界顶尖的一流大学,但卓越并不意味着完美,在培养未来社会的杰出领导人才方面,哈佛也有很多不足。本书坦承了哈佛存在的不足。
本书作者哈瑞·刘易斯在哈佛从教30多年,其间的1995~2003年担任了哈佛大学下属的专司本科生教育的哈佛学院院长一职。他认为,在争夺优质师资和生源的过程中,哈佛忘记了本科教育的根本目的——把年轻人培养成富有学识、智慧、能为自己的生活和社会承担责任的成年人!然后,刘易斯教授从课程设置、沟通合作、生活咨询、分数贬值、校园犯罪、贫富差别、大学体育、领导风格等问题着手,分析了哈佛这所著名大学本科教育的不足之处。他还细致地回顾了这些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揭示了哈佛的办学目标如何从真正的引导性教育向迎合学生需求的“用户至上主义”方向发展的,并提出了进行教育改革的迫切性。
“空瓶子”课改?
大学课程是学生获得学位而必须参加的一系列学术计划,课程传达的是一所大学对教育本质的诠释,所以,课程改革的决策会引发冠以大学教育目标的“战争”。2002年10月,哈佛开始了由校长劳伦斯·萨默斯主导的课程改革,2005年春推出了《新通识教育课程改革方案》,方案规定学生需要在原有通识课程的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中,各选择3门科目,科目允许各系开课,而不必为通识教育特设,同时,降低对学生必修课的要求,增加学生的选择机会,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选课的灵活性,并特别关注课程的国际化和科学革命的影响。刘易斯认为,这次课改是一个没有实际内容的“空瓶子”。为什么如此?
他认为,萨默斯校长主导的新通识教育课程,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各系可以任意给“空瓶子”里放各种材料,“新课程完全放弃了共享知识、共享价值观甚至共享抱负的理念。由于没有明确给定学生需要知识的轻重缓急,哈佛实际上在向世人宣布:在21世纪,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可以不知道‘基因’、‘染色体’和‘莎士比亚’!”此外,20世纪40年代的“红皮书”提出哈佛应培养“作为自由社会的公民”,而新课改方案提出,哈佛现在的教育目标则是“将学生培养成为全球化社会的公民”。刘易斯教授对此颇有微词,他说:“通过通识教育让人的思想更自由、心灵更高贵,这一直是哈佛教育的基本原则。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出现的重要现象,学生当然需要理解这一点,但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并不能取代民主理想的重要性。”刘易斯质问,以哈佛为代表的“这些重点大学是否在忠实地履行国家赋予他们的职责?”他说,哈佛的核心课程甚至没有给学生提供认识自己国家的机会。
从客观的立场上来看,刘易斯的担心不无道理——培养合格的公民、延续国家的希望是教育的基本责任,正如我国高等教育所强调的使命——“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格人才”一样。但是,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重要组成,大学在服务国家建设的同时,更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创新知识,培育和传递人类普遍的道德准则和终极价值观。
“取悦学生”
哈佛的教育过程缺乏长远的打算和远大的目标,在课程设置、学生评价、校园文化、道德教育等方面,总以“提高学生的满意度为工作目标”,总是设法“取悦学生”,而不是帮助他们成长,“因为学生只看到眼前的需求,而我们总是有求必应。我们没有告诫他们抬头望望长远的目标”。“我们的失职导致学生的性格和道德不能健康发展。这种失职有时是愚蠢和可笑的,有时贻害无穷。”……在刘易斯教授的娓娓道来中,我们会看到作者丰厚的教育经验,及对教育的深刻理解,而通过其恳切的言辞,我们会体味到作为一位教育家所具有的责任感。
为什么哈佛大学处处以“取悦学生”、“迎合学生的需求”为工作目标?哈佛为什么从真正的引导性教育向迎合学生需求的“用户至上主义”方向发展?刘易斯认为,这一方面源于“研究代替教育,成为大学的基本职能”,另一方面源于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前者促使大学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争取科研经费、做出研究成果方面,无暇顾及学生个体的全面发展;后者使得市场经济的规则渗透进了大学,并成为大学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更深的层次上,“取悦学生”的文化源于哈佛领导层及教师们对“尊重学生选择自由”的片面理解,“学生的学习越随心所欲,教师的教学也就越随心所欲……自由是有条件的,真正的自由并非随心所欲。自由是选择和责任、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之间的一种平衡。今天制定哈佛学院教育计划的人,口口声声说‘自由’、‘灵活性’、‘机会’,但他们忘记了自由的根本所在。这些人的目标仅仅是为提升哈佛在学生调查中的满意度。”
对此,莫顿·凯勒和菲利斯·凯勒在《哈佛走向现代:美国大学的崛起》一书中说,“没有一个机构是完美无缺的,哈佛大学没有去隐藏缺点……适应智力、文化和社会变化的能力是现代哈佛成功的主要源泉,也是它的问题和不满的主要源泉。”高等教育大众化、国际化和全球跨国企业的崛起是20世纪后期以来的时代主题,可以看出,哈佛的问题及人们对哈佛的不满,正源于它在适应这一主题的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失误。
充满理性的工作思路和目的
全书中,作者关注的主题是哈佛的本科教育,关心的是“把有依赖性的年轻人培养成为有智慧的成年人”。他把完成这一使命的关键力量放在哈佛的领导人身上。他说,一个大学需要观念和目标的指引,需要一个充满理性的工作思路和目的,“大学领导人除了自身学术成就外,还必须具备认识自我的能力、成熟的处事方式、人格的力量及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肚量。为了把充满希望的大学新生培养成社会英杰,学校领导人不只应该是聪敏和有成就的专家,他们必须是有智慧、成熟和善良的人。围绕大学组成的家庭——家长、学生、教授及学校主管部门都应该有权判定大学领导人是否达到上述标准”。“哈佛最需要的是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理想主义,这些职能来自于学校的最高层”。回顾哈佛历史不难发现,正是在埃利奥特、洛厄尔、科南特、普西、博克等优秀教育家的执掌下,哈佛才一步步成为世界大学的皇冠。
虽然刘易斯对哈佛的批评,部分源于他与时任校长劳伦斯·萨默斯的观念冲突和不合,他对萨默斯的成见也显露在全书始终,但人们也有理由相信,刘易斯对哈佛的批评,不仅仅是个人积怨的发泄。其实,针对萨默斯校长的批评仅限于新课程改革方面,面对哈佛从一个卓越的教育机构向商业机构的嬗变、哈佛文化中消费者至上的倾向等问题,作者都作了透彻的分析和真诚的反省,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刘易斯深怀敬意——正如哈佛教育学院霍华德·加德纳所说,刘易斯是一个勇敢的人,写了一部大胆的书。这是作者作为教育家所具有的责任感的驱使,也是美国良性的教育生态和宽松自由的言论环境的客观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