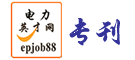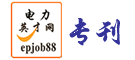故事的主角当然是民工子弟学校,或者叫打工子弟学校。一样,人们都知道说的是哪一个群体。这个学校选择了在教师节的第二天倒闭,只是出于不影响节日气氛的美好愿望而已。屈指算来,已成为中国社会传统节日的教师节,在这个国度已经排到了第23个了。
第23个教师节前后,北京昌平新龙打工子弟学校出现了严重的财务危机,过不去这道坎儿,校长宗宝平正式向当地教委提交了倒闭报告。(2007年9月12日《京华时报》)
看上去这似乎是一个孤立的个例。从2007年7月开始,这个已经办了5年的学校先后经历了强拆、重建、资金链断裂。在拿不出10万元租金的窘迫中,房东断水断电,学校只能停办。然而,从更大的背景来看,这个个例或许就是北京30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的代表,其中,能够自负盈亏的不足一半,有办学资质的只有62所,几乎所有的打工子弟学校都面临资金困境。很多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能够走的稍微远一点。
上边的故事中,蕴藉了太多的悲情。这种悲情每每让人泪流满面。在召集全校教师开会宣布倒闭的消息时,校长宗宝平和老师们一样泪水涟涟,“我是流血不流泪的男人,但是今天,我实在太难过……请各位老师一定要配合,现在有学校愿意接收学生和部分老师。”而在向学生宣布学校停办的决定时,“班主任刘洋再也忍不住了,泪流满面。几名女生也埋头趴在课桌上,小声哭起来,男生们也都红了眼睛。”
为什么打工子弟的教育总是充满着泪水和悲情?为什么我们的城市对这个群体就不能多一些呵护和关爱?
大约从1999年开始,关于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学校的报道就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那些包裹着沉甸甸的同情和焦虑的文字,一度让社会为之震惊,也引发了很多有识之士的政策建言。然而,快10年过去了,情况依然没有多大改观。国家对于教育的政策之光,很难照拂到这个边缘的群落。以新龙学校为例,困境最后以昌平教委借款10万元得到暂时解决,但昌平教委同时也表示,对于打工子弟学校,教育主管部门并无必须的义务,资助新龙学校是个例外。
2000年冬季,我也曾经采访过北京部分打工子弟学校,那些学校大都徘徊在生存的边缘。很难想象,在文教发达的北京市的一些角落里,还存活着如此简陋的所谓学校。特别是,当我看到某年春节晚会上一群民工子女用稚嫩的声音与城里的孩子“比明天”时,我的悲怆难以言表,置身于几乎是原始教育条件下的孩子,你拿什么与人家比明天?仅仅是永不服输的精神么?
很有一些论者以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看待这些打工子弟学校,并指责其为什么不利用装备精良的公办学校,这些说辞,大抵超越得很。基本上于事无补。办学的窘迫,求学的艰难,因为其代表了部分公益的价值、文化的传承乃至社会公平的诉求,往往更能够凸显出浓重的悲壮意味。这种悲壮像山野里的草和树一样原汁原味,真切可感,很难以单纯的市场经济竞争理论来进行匡正。
来自财政部提供的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共安排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资金361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安排150亿元。免去了5200万名学生的学杂费,为3730万名贫困学生免费提供了教科书,对780万名寄宿学生补助了生活费。(新华社2007年9月9日电)对于以民间投资为支撑的打工子弟学校而言,这些资金却是遥不可及,或者说,这些已经存在了10多年的草根学校的办学主体地位都岌岌可危。何谈惠及?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提速,我们的城市如何来“化”大批涌进城市的人群?以往界域分明的城市教育和农村教育之间,有没有一个融通的好法子?实际上,打工子弟学校在这方面可谓居功甚伟。我们真诚的希望,我们的教育政策设计应该正视这种努力,放弃以往僵硬的界线,也让国家教育的政策性投入关照一些这个群体。既要锦上添花,更应该雪中送炭。只有切实的扶持才能迅速提高这些学校的教育水准,那些民工子弟也才有足够的底气与其他的花朵比试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