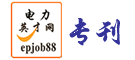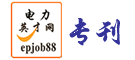人教版第六套教材。人教社供图
67家出版社出版的175套教科书,学校可以随便挑选适合自己的。
这在3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那时,拥有一本教科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一些学生参加文革后的首次高考,即因为没有合适的教科书而落榜。
那时仅有的教科书中,孔子以反动思想家的面目出现。
文革结束后,国家专门组织了一个庞大的班子重新编写教科书。如今,在中国古代史中,孔子成为了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30年中,教科书几经嬗变,如今正进入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
没有课本的日子
1977年的冬天,高三学生于红艳和姐姐抱头痛哭。姐姐一边哭一边指着书架上的一堆“课本”告诫于红艳:“这些东西根本没用!”
在文革后的首次高考中,姐姐落榜了。为了帮助女儿复习,于红艳的父亲托人四处收集了几乎各科的教科书。
这些由各地“革委会”自定自编的课程和教科书,封面上无一例外都是革命领袖的“最高指示”,无论是数理化还是文史地,大段语录和套话均占据了正文的大部分,真正的学科内容非常少。
在于红艳的印象中,物理教科书被简化成了“三机一泵”(拖拉机、柴油机、电动机、水泵),生物教科书则简化成了“三大作物(稻、麦、棉)一头猪”。
姐姐放弃了继续参加高考,顶班进入县城的造纸厂当了一名工人。这对于红艳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上大学同样也是她的梦想。
最终,还是于红艳的老师翻出了自己上世纪50年代末上大学时的书本,从中摘抄了一些要点,用蜡纸密密麻麻地刻了几页“复习提纲”,权当教科书。更多的内容,老师会板书在黑板上,于红艳和同学的课余时间,就是在不停地“抄书”。
凭着刻印和手抄的“教科书”,于红艳在1978年的高考中,考取了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
进入大学后,于红艳用自己第一个月的师范生补贴,在大学的书店里一口气买了20多本教科书,寄给自己的高中老师和落榜同学。
当时,距离于红艳最近的一套全国通用中小学教科书,出版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期,这套教科书文革后不久就被停止使用。
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全国的中小学生都遭遇着和于红艳一样的尴尬,没有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教科书。编写新教科书
于红艳并不知道,在她为教科书发愁的时候,一个由20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的“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正在进行。这实际是一个编教科书的临时集体,承担着1978年版国家统编十年制中小学各科教学大纲和教科书的研制、编写及出版。
年近不惑的王宏志被从北京市教育局教材组征调回这个集体。1961年她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人教社,编写了文革前的历史教材,主要编写小学中国古代史部分。文革期间,一直承担中小学教科书编写、出版的人教社一度被撤销建制,数百名编辑星散到全国各地,王宏志在下放数年后回到北京。
这是邓小平1977年复出主持工作后,首抓的第一批重大事项——要重视中小学教育,“关键是教材”。他要求教育部尽快组织人力编出一套统一的中小学教科书,从1978年秋季起供应全国,保证“课前到书,人手一册”。
中组部一纸调令,包括王宏志在内的人教社原有教材编辑人员很快被从全国各地召回北京,并又从全国18个省市区的大中小学借调了大批骨干学者和优秀教师。由于人员众多,且人教社原有办公楼被占用,邓小平直接批示将西苑宾馆的一栋楼特批作为办公地点。
王宏志和一批在北京的专家学者率先进驻西苑宾馆9号楼,此后的一段时间,陆续有熟悉或陌生的面孔加入。
众人很快就忙碌起来。一批编辑人员被分派到13个城市,对教学大纲和教材的制定、编写工作展开调研。教育部也特聘了45名各学科的著名专家作为顾问,包括苏步青、周培源、叶圣陶、吕叔湘等等。
编辑们很快遇到了问题。由于文革的影响,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体系濒临瘫痪多年,尤其在自然学科领域,一经恢复,应该选择什么内容进入教材,沿袭60年代初老版教科书的知识体系,还是选择新知识?对于新知识的获取和判定也无从下手。
邓小平再次拍板:“要引进外国教材,吸收有益的东西。”并且从紧张的国家外汇储备中拨出10万美元专款,让我国驻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等使领馆,协助选购一大批各国最新的中小学教科书,并尽快空运回国。
这些“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毒草”,让编辑们目瞪口呆——近30年的中西隔阂,我们已经被世界最前沿的文明成就拉开了这么长的距离。
数学编辑发现,西方国家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在中学教材中引入微积分和概率统计的初步知识;而生物编辑则在美英等国的高中生物教材中,看到从“分子水平”阐述生命活动本质和生命活动规律已经成为常态。这些内容,在当时国内的大学专业教材中,也不常见。
编辑们开始补课,并将这些散发着新鲜味道的知识,小心地移植到自己即将出版的新编教科书中。
此时的“教材编写工作会议”,已从西苑饭店搬到了香山饭店的中式瓦房。仍是每人一张床加一张桌子,人教社的图书馆几乎搬到了香山脚下。王宏志等人教社的老员工还把家里的大量藏书带来,每天几乎都在翻书查资料写教材。
1978年秋天,小学、初中和高中起始年级新生,如期拿到了人教版新书。直到1980年,各学科各年级的教科书全部出齐。
孔子地位的转变
写好的课文会在小组中传阅,并以会议的形式进行讨论。王宏志所在的历史组由人教社资深专家苏寿桐带队,有16个人。
“落笔之前的总体编写原则,就无法形成统一意见。讨论来讨论去,发现很多问题没法解决,需要请示。”王宏志说,原本历史学界的很多定论在文革期间被“极左”思潮弄得很混乱,大家觉得很多文革期间的用词都无法使用,需要中央高层统一意识。
针对儒法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内部的路线、历史教材的下限等六大问题,历史组反复酝酿讨论,最终将自己的看法综合,起草了一份名为《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几个原则性问题如何处理的初步意见》,呈递中央审查。邓小平批示“原则同意”,这才定下了很长一段时间历史教科书编写的基本准则。
在很多具体历史问题上,历史组成员都存在争议。王宏志就对当时朝代章节的划分持不同意见,她认为秦汉应该作为单独的章节,与战国分割开。“但我是里面最年轻的编辑,那些老师坚持己见,我资历太浅,插不上话。”王宏志笑着摊了摊手。
“毕竟文革那么多年,一直受‘极左’的思潮影响,当时大家还是小心谨慎的。”王宏志说,并不是所有的历史都一下子扳了过来,孔子的情况就是如此。
只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才明白“批林批孔”的浪潮是多么的汹涌,“孔老二”的名声有多臭。1974年北京市小学常识课本,就直接将《反孔和尊孔斗争的故事》作为历史教材。
1978年3月第一版、6月第一次印刷的教材中,对于孔子一章的标题仍然是“孔子的反动思想”。正文中提到“他提出了一套挽救正在崩溃的奴隶制的反动主张,创立了儒家学派……孔子的反动思想,后来被统治阶级改造和利用,成为维护封建制度和统治人民的精神工具。”当时历史组内部就产生了激烈的碰撞,不少人提出应该对孔子有更加客观的评价。
仅仅9个月后再次印刷的教材中,标题已变为“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不过在肯定孔子的同时,特别强调他维护等级制度,表述并没有质的变化:“孔子的思想,后来被统治阶级改造和利用,成为维护封建制度和统治人民的精神工具。”
1986年版中,对孔子思想“精神工具”的提法也被取消,表述为:“他的学说后来成为我国2000多年封建文化的正统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
2001年版中,标题变为“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对他给予充分肯定:“后来,孔子的学说成为封建文化的正统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影响极大。”
这一系列的改变,缘于时代的进步和人们历史观念的改变。不再需要中央高层特意“打招呼”,王宏志等人也不必再屡次向上请示。“思想越开放,改革开放越深入,我们对于很多事情的认识才更全面,评价也更客观。”90年代已经从人教社副总编位置退下来的王宏志说。爱情诗进入教材
于红艳1982年毕业后,被分配回家乡江西上饶,在一所市重点中学当历史老师。头几次登上讲台,让她自信心很受挫。因为她觉得手中的这本教材很难,自己没把握了解透彻,更不用说教学生了。有前辈安慰她说,不只你一个人觉得难,很多老师尤其是理科老师都有这样的反映。
这一时期,人教社陆续收到各地的反馈,表示78版十年制的教材内容过多过深,老师们吃不消。
“我们有些低估了文革十年对师资力量和基层教育设施的摧残,而且,编辑们太想把更多更新的知识传授给孩子了。”一位人教社前任领导总结说。之后,教育部采取了改变学制、精简内容等多种措施,出版社也对教科书进行了多次修订和改变,以缓解这种状况。
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随之教育部颁布了新的课程计划和教学大纲。人教社开始编写酝酿已久的“九年义务教育教科书”,希望编写一套难度适中,适用于全国大部分地区、大部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全新教科书。这套书的显著特点是从32开的小本变成了16开的大本,同时增加了大量的插图,生物、历史、地理等科目采用了彩色或双色印刷。看着就漂亮了许多。
这套教科书贯穿了整个90年代,几乎所有“80后”都使用这个教材。今天,这些“80后”逐渐进入社会成为时尚文化的主流,“九年义务教育教科书”中的一些特色被追捧。高中语文教科书收录的《致橡树》,来自于现代诗人舒婷。这首现代爱情诗歌进入中学语文教科书,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讨论。
人教社中学语文室的编审庄文中还记得当时的争议,甚至在他力主选用该诗时,就有同为编审的同事表达了担忧。“我就对他们说,改革开放嘛,试验了再说。结果,教学效果很好,师生都喜欢。”庄文中说,当时的语文教科书里并不缺乏爱情题材,比如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国古代的《孔雀东南飞》,但都是爱情悲剧,应该有一篇意象鲜活、更具人性化的现代爱情作品。
让庄文中高兴的是,当时河南一所中学,语文教师在讲述《致橡树》时,还引导学生自己创作有关爱情的作品,并将这些作品寄给了舒婷。舒婷特意给他们回信,让师生都非常兴奋。
“高中生已经有了自己的世界观,引导他们学习优美的爱情诗,高雅一点,总比唱‘爱死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好多了吧。”庄文中赞成引入文学性强的作品进入中学语文殿堂,比如金庸小说、先锋派文学等,在选读教材中供学生阅读,以激发学生对文学、情感的多元感知。
2000年春天,江泽民特地调阅了人教社出版的中学历史、地理教科书。随后,他指示全国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人手一套,加强史地知识的学习。这让人教社编辑们欣慰和兴奋。
随着新一轮的课程标准系列实验教科书的逐步推广,2003年之后,这套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教科书淡出历史舞台。
教材的百家争鸣
今天,于红艳已经成为学校历史教学带头人,特殊的经历使她对教科书的发展保持着关注。在她看来,现在的历史书和30年前相比变化太多——最早只要是农民起义,就肯定有大量篇幅,现在只剩下陈胜、吴广以及李自成。
在人教社根据教育部新制定的《历史课程标准》所编写的2001年版中学历史教科书中,讲授抗日战争的一课名为“血肉筑长城”,其中的重大变化,即以“全民族的抗战”的线索统摄全文,取代新中国成立以来一贯的表述方式——“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片面抗战路线”和“全面抗战路线”、“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同样的描述变化还包括洋务运动、义和团等等。
于红艳甚至不习惯了。多年来对历史词汇的学习和积累,让她有些无所适从。
更让于红艳不习惯的,是除了人教社的教材外,其他几十家出版社也开始出版教材了。
这个改变从1986年初见端倪。人教社编审一体的制度被打破,为了使教材多样化,以适应全国各地的需求差异,教育部成立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统一规划和审查教科书。不同出版单位甚至个人都可以根据教学大纲编写教材,只要通过国家教委的审查,就可出版并流通。
针对中小学教科书,国家和地方还先后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包括选用制度改革、限价措施、发行招标、教科书循环使用等等。
于红艳倾向教科书实现真正的有序竞争,毕竟竞争有利于全面提高教科书的质量,最终学生受益。当然,她对于历史教科书的改革还有更多期待。
王宏志、庄文中正打算和人教社的老同事们一起,编写一部《新中国教材史》,记录教科书这些年走过的路,以及自己或者更多人,和教科书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