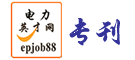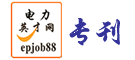郑章军在北京市海淀区小月河曾经租住过的亿展学生公寓。记者 来扬摄
随着《蚁族》一书渐为人知,“蚁族”这个新词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有人惊叹:“原来我们就是‘蚁族’!”也有人开始思考:原来还有这么一群“蚁族”。
学者廉思和他的团队,历时两年,对北京市唐家岭、小月河、马连洼等多个大学毕业生聚居村进行了调研。“蚁族”这一群体是怎么形成的,他们的生活状况怎样,他们是否会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中国青年报记者日前专访了廉思。
绝大多数是“80后”
中国青年报:“蚁族”是个比喻,你能否给这一边缘青年群体画一个像?
廉思:“蚁族”这个名字是在今年3月团队的一次讨论时提出来的。我在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时,使用的是“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
从名称上可以看出,这个群体具有三个特点:高校毕业、低收入和聚居。这三个特点使该群体区别于“校漂族”。后者虽同样也是高校毕业生,但主要以考研为目的,多半散住在学校内或校园周边。“校漂族”仍会使用自习教室、食堂等高校的部分资源,但我们的调研发现,“蚁族”多半是全职工作的高校毕业生,不再使用高校的资源,住的地方一般远离高校,且居住方式呈“聚居”状态。
如果让我来给这一群体画像,他们绝大多数是“80后”,收入不高,生活拮据,工作不稳定。具体来说,他们有的毕业于名牌高校,但更多来自地方和民办高校;拿着1000元左右的工资,租着每月300元的床位,每天吃两顿饭,到工作单位要坐两个小时以上的公交车。绝大多数从事保险推销、餐饮服务、电子器材销售等低收入工作。有的完全处于失业状态。他们生活条件非常差,缺乏社会保障,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
中国青年报:你的团队曾对这一群体进行过问卷调查,是否有一些数量上的精确表述?
廉思:根据我们对546份有效问卷的统计,“蚁族”群体的年龄集中在22~29岁之间,以毕业5年内的大学毕业生为主,税前月平均收入主要集中在1000~2500元。同时,“蚁族”的基本生活消费相对较低,每月的房租平均为377元,饭费为529元,月均花费总计1676元。多数被调查者都处于收支平衡或略有结余的状态。
就工作单位来讲,“蚁族”大部分成员(89%)任职于私、民营企业;其中有16.5%的群体成员的工作单位性质为个体经营。有32.3%的调查对象并没有与工作单位签订正式劳动合同,36.4%没有“三险”的保障。
绝大多数来自农村或县城“弱势阶层”
中国青年报:他们大都来自哪里?
廉思:被访者绝大多数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其中河北、河南、山东等地最多,大部分系外地高校毕业后到北京找工作。从户籍来看,绝大多数人来自农村或者县城,但多数通过升学取得了城镇户口,又以外地城镇户口为主。
中国青年报:他们的家庭背景又是怎样的?
廉思:从群体整体情况分析,“蚁族”中较低阶层家庭的子女更多地获得较低水平的高等教育资源。整体中父亲职业阶层为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分别只有3.5%和8.5%,其中管理人员的比例低于全国的该阶层比例;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只占到8.2%。可见,这个群体是以中下等阶层家庭为主,他们的现状似乎是父辈的再现。同时,从就读学校质量来看,超过90%的毕业生毕业于非重点大学。
从群体内部情况分析,父辈家庭背景影响子女教育获得,分化路径沿着本/专科、热门/冷门专业、国民教育/非国民教育系列三个维度进行。管理阶层、专业技术人员等优势阶层的子女在更高学历中(如本科和研究生)的辈出率更高;而个体、失业退休者以及工人等较低阶层的子女在较低学历(如专科)中的辈出率更高;此外,商业服务业、农民等较低阶层的子女在各个学历中的辈出率都很低。
“帘子里隔着的性”
中国青年报:我们在走访小月河“聚居村”时发现,许多公寓对外出租的床位“男女有别”。女性居住的楼层入口贴着“男士止步”的告示,但走进一些男性居住的房间,有时会不经意看见床边的高筒皮靴。
廉思:课题组在调研中也曾遇到在男性宿舍留宿女性的情况,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宿舍里同时居住四个男人和一对情侣。虽然居住空间隔着帘子,但是性生活的质量以及对他人的影响不容忽视。
调查显示,“蚁族”中未婚人数占调查对象的93%,在未婚者中有49%没有恋人。与异性同居的人占到被调查对象的23%,但最近一个月内有性生活的人占到被调查对象的33%。从这些数据对比可以看出:“蚁族”结婚的比例小于与异性同居的比例,与异性同居的比例小于最近一个月有性生活的比例,最近一个月有性生活的比例小于有恋人的比例。
中国青年报:“蚁族”是否存在“婚恋困境”?
廉思:“蚁族”经历过大学阶段,有恋人的比例应该明显高于大学生群体,但与大学生群体对比分析后发现,该群体与大学生群体在此方面差距很小。“蚁族”的收入水平较低,社交圈子小,恋爱对象的选择范围小,整日忙于找工作或工作,谈恋爱的机会也少。如果经济条件允许,该群体的结婚比例应该比较高,但目前只有7%。可见,“蚁族”绝大多数正处于生理旺盛期,渴望同异性交往,在恋人或夫妻方面得到感情上或生理上的支持和安慰,但由于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没有固定的住所,他们无法在婚姻和恋爱的问题上考虑更多,所以大部分毕业生选择了单身或同居的方式来生活。
“性—爱情—婚姻”的现状影响了“蚁族”对生活的满意度,性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影响身心健康。即使有性生活的人,其性生活的质量也要受到性生活的地点和环境的影响。如果长期压抑,可能导致犯罪,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青春为何停靠“聚居村”
中国青年报:“蚁族”到底有多少人?
廉思: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课题组研究表明,仅北京地区保守估计就有10万人以上。此外,上海、武汉、广州、西安等大城市也都大规模存在这一群体。
中国青年报:在你看来,唐家岭、小月河等地聚居的“蚁族”是怎样形成的?
廉思:原因可能有很多。从宏观原因来看,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很大。另一方面,“蚁族”的形成也受到就业形势变化和就业政策调整等因素的影响。例如,我国高校自1999年开始扩招,自2003年起,每年都有较前一年更多的毕业生涌向社会。但近年来,社会对高校毕业生需求的增长速度并没有赶上毕业生数量增加的速度,同时,毕业生就业的市场需求情况并没有及时成为专业设置、招生人数划定的“风向标”,使得许多接受了大学教育但却没有一技之长的高校毕业生面临就业尴尬的局面。
中国青年报:他们为什么要聚居呢?
廉思:现有的“聚居村”所在地房租低廉、交通便利,同学、老乡相对集中,群体间容易形成认同感等。此外,由于环城带地区交通便捷,生活成本低廉,可开发利用土地相对较多,开发建设速度加快,就业、创业机会相对较多,加之这些地区大量合法和违法建设的出租房屋,使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此落脚成为可能,因而形成聚居。
中国青年报:说白了也就是房价的问题?目前北京市对外地来京大学毕业生的住宿方面有无相应的规定,如是否将这个群体纳入廉租房的受惠范围?
廉思: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因为户口限制,廉租房制度惠及不到该群体。北京市已经意识到相关问题,正在积极地通过立法解决。
他们不应被社会忽略
中国青年报:我们知道,蚂蚁的群居是有组织的,工蚁采集食物,兵蚁保卫家园,它们各司其职,都听蚁后的调遣。但在“蚁族”里,实际上并没有一个“蚁后”式的人物,而是各行其是。你怎么看待这种差别?
廉思:这种差别确实存在,但我们采用“蚁族”一词来命名该群体,主要是基于两者之间的共性,而共性是主要的。我们调查的情况是,“蚁族”目前并没有类似蚁群中蚁后地位的“带头大哥”存在,而这也是我们要极力避免的问题。
中国青年报:我们在采访中发现,聚居村中的大学毕业生不仅是松散的,而且是流动的。
廉思:“蚁族”存在“转折年”现象。“聚居村”是一个流动者的聚居地,主要以毕业三四年内的“蚁族”为主体,第四年后的毕业生人数会大幅度减少,毕业五年以上仍然住在聚居村中的“蚁族”只占了6.8%。因此,毕业后第三年或第四年是“聚居村”中“蚁族”的“转折年”。所以,我们应高度关注毕业三四年内高校毕业生的心态和动态,这对于消除社会隐患是相当重要的。
中国青年报:“蚁族”成员平时怎样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
廉思:“蚁族”作为“80”后社会群体,对网络的熟练程度是整个社会中较高的一个群体。“蚁族”在遇到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事情的时候,大多会选择采取行动来进行自身利益诉求,而不会选择沉默。而且,这一群体大多倾向于通过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但同时,这一群体对于罢工、游行示威等较为激烈的集体行动方式的赞同程度都较低。
虽然这一群体目前参与集体行动的倾向不高,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参与集体行动的倾向,也并不意味着如果任由这一问题扩大,他们未来参与集体行动的倾向依然很低。
在相对剥夺感强烈,生活满意度低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改善中国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生活状况,任由其不满情绪累积,那么,未来各种怨恨高度积累、叠加达到集体行动的临界水平时,一旦出现某一特定事件,在特定情境下,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可能就会发生。
中国青年报:他们希望政府或社会提供哪些方面的帮助?
廉思:29.27%的受访者把“平等的工作机会”作为希望政府提供帮助的首选,其次是“住房政策的倾斜”和“平等的户口政策”,其他方面有“医疗政策的倾斜”、“职业技能的培训”和“充分的就业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