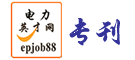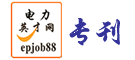站在眼前的女孩神色坚定、目光逼人。虽然长途的奔波让她略显疲惫,但面对眼前的咨询协议和测评报告,她还是显示出了自己的敏锐。她很快、很凌厉地提出自己的问题:这个协议签了字是不是就有法律效应?你们的服务目标具体是指什么?时限规定的依据有没有国家标准……
直到所有问题都得到满意的回答后,她才在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若文。她咨询的问题是:要不要离职。
半年前,若文是个
欢快的幼儿教师,活跃在南方某个小城市。刚刚毕业的她年轻、活泼,惹人喜爱。可是那股热情燃烧得太快了,仅仅3个月,她便沉寂了下来。每天对着镜子问自己:我每天到底在干什么?
“和小孩子接触是件没有成长的工作,每天只能重复自己都觉得像傻瓜一样的游戏,说着幼稚话语。工作3个月,我觉得自己倒退了3年。连句成人的话都几乎不会说了。我实在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若文越说越激动,声音都有些发颤。
“那你当初是怎样选择了当幼师的呢?”
提起当初,有一瞬间,若
文的脸上由激动转为愤怒。但很快地,她又把那种愤怒压了下来,用尽量平和的语调讲起自己的故事。
“这话说起来就长了,我的家里有两个孩子……”
若文在6岁之前是和姥姥在一起生活的,原因是妈妈和奶奶处不来。妈妈不想让奶奶太多过问孩子的事,于是经过权衡就留下了大若文两岁的姐姐自己带,而将若文交给姥姥。虽然妈妈每个月都会来看若文一次,但她幼小的心里仍然觉得自己是被妈妈抛弃的孩子。每次,妈妈走的时候都会骗她说,很快再来,但那个“很快”永远不会少于一个月。
这是个漫长的适应过程,但若文终究适应了。她开始依恋姥姥,不再那么盼望妈妈。可是,她很快6岁了,要上学了。命运再次让幼小的她从刚刚建立的亲密中脱落,因为她必须要回家才能保证有好的学校念书。 那又是一次痛苦的经历,小若文被骗上车、骗回家。直到走进楼梯口,她才醒过神来,伏在扶手上大哭,因为姥姥家是没有楼梯的。
作为孩子,若文没有选择的权利,她只有再次地适应。
姐姐在她回来之后,就开始变得身体虚弱,总是得病,妈妈不得不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姐姐身上。妈妈忙,若文有时也不得不加入照顾姐姐的行列,成为她的小保姆。但姐姐似乎并不喜欢若文,总是设法骗她、欺负她,而后又向妈妈告状。由于和奶奶的关系,他*的脾气特别不好,总是在若文面前发火,甚至打她,所以谈到和姐姐的关系,若文总是说“一般”。
若文上初三的那年,姐姐恰好在一个重点高中读高二。那个重点高中的升学率几乎是百分之百。拮据的父母于是和若文商量,是不是选一个其他的方向,早点就业,因为家里供不起两个大学生。若文不甘心啊,她学习一直很好。但谁让她是老二呢?体弱的姐姐比她更需要轻松些的工作。(这至少是父母对上大学意义的理解)于是在父母的帮助下,她千挑万选终于选了幼儿师专,据说可以包分配。“我的命总是不好!”说到这个的时候,若文叹了一口气。刚才那个伶俐的姑娘,这会儿成了多愁善感的林黛玉。“我又受骗了!”
那个师专在若文上学的第二年进行了改革,原来说的包分配全成了泡影。“我再也不轻易相信别人了……”这话让我想到她签协议前的谨慎。“你说你工作的前3个月还是很有热情的?”“对!我那时傻乎乎的,被老园长和几个优秀教师的报告给打动了,以为自己要真的献身于幼教事业。现在想起来……唉……真傻,不过……也挺快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