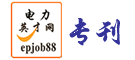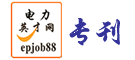八十年代,一首摇滚歌曲《一无所有》不知道打动了多少人的心扉,而它的演唱者崔健不仅一举奠定了中国摇滚歌手大哥大的地位,更是成了“一无所有”的代表人物。但是前几天偶翻以前的旧杂志,方才知道(恕我孤陋寡闻)这首歌背后还有一些小插曲。原来崔健不是中国人,也不是真的“一无所有”, 他是韩国人,他的父亲是韩侨,母亲出生在釜山,当时的韩国总统卢泰愚还曾因为他的成绩而接见过他,并送过他手表衣物等等。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同意一位歌迷所说的一段话:……崔健到底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歌唱就值得怀疑了。他的歌失去了原质的内容和真实的基础,痛苦和反抗就显得太不真实了,事实上崔健完全没有必要像歌中表现的那么痛苦,那么声嘶力竭地反抗,他随时可以到韩国去过一种比较优裕的生活,总之他不适合再做一个“一无所有”的代言人了。
无论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还是简单的血统论,关键是崔健的真实身份已经无法支撑起这首歌中所表达的一个民族沉重、苦难、幸福和希望的生存状态,尽管他演绎的《一无所有》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在完美的背后却是冷冰冰的虚假和做作。
与《一无所有》相类似的,应该还有《瓦尔登湖》。自从梭罗的《瓦尔登湖》问世,不知道引起了多少人对他所描绘世界的向往。勿庸质疑,隐居、独处、脱离功利的世界,是所有人所渴望的,而《瓦尔登湖》恰恰给我们昭示了这样的主题:对文明的挑战,对城市的拒绝,对社会的疏离,对现实世界的厌倦。这一切看上去是多么的洒脱和独立于世。但实际上,现实中的梭罗根本就不是这样,甚至可以说相差很远。在瓦尔登湖隐居其间,梭罗几乎每天都要到康德镇上转悠,每天都要回到他父母家里享受现代的生活。他的文友们更是经常光顾他的小屋,在湖畔开野餐派对。这些都说明,梭罗并没有过他所谓的远离现代生活的独居生活,他既没有真正体验没有人间烟火的世界,也没有去刀耕火种,在他的内心世界里始终就没有脱离现代物质生活对他的诱惑。而瓦尔登湖,也不是我们想象的世外桃园,更谈不上远离人烟,它其实离著名的康科德镇只有两英里,湖畔就有通往菲茨堡的火车。离他最远的邻居也不过只有一里路,去他的父母家,大概十分钟就够了。就是这样的一处湖泊,真的很难让我们想象出梭罗所谓的远离城市和现代文明。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梭罗自己曾说过的话:我来到这片森林是因为想过一种省察的生活,去面对人生最本质的问题,看看是否有什么东西是生活必须教给我而我没能领悟到的,想知道假如我不在这里的话,当我临终的时候,会不会对自己并没有真正的生活过毫无觉察。
这样的话语,除了虚假之外,还有什么呢?
梭罗是虚伪的,《瓦尔登湖》是虚构的,梭罗只是在自己的相象中给我们虚构了一个世外桃园,我们就这样认真的进入了,而且还无法自拔。
其实无论崔健的《一无所有》,还是梭罗的《瓦尔登湖》,我们都无法苛责他们的人生经历和他们作品的统一性。也许只有保持适当的距离,才会把内心的世界演绎的更完美更到位。而我们对他们的追风和膜拜,恰恰是我们太注重眼前的这些荣华了,却忽视了这些荣华背后那些虚无的东西。